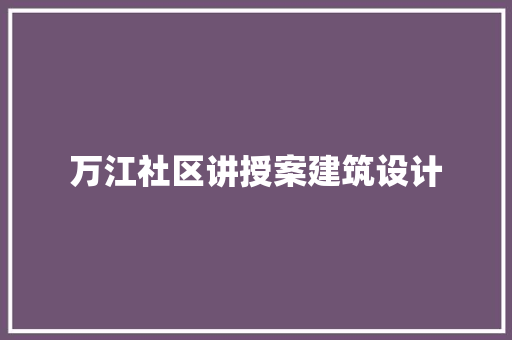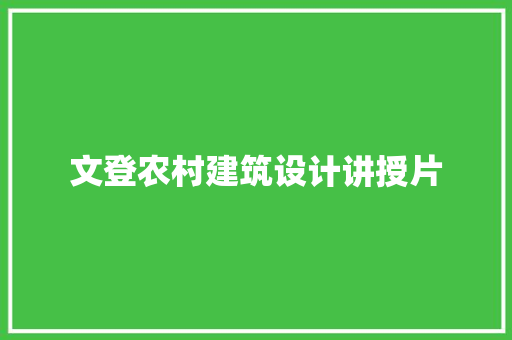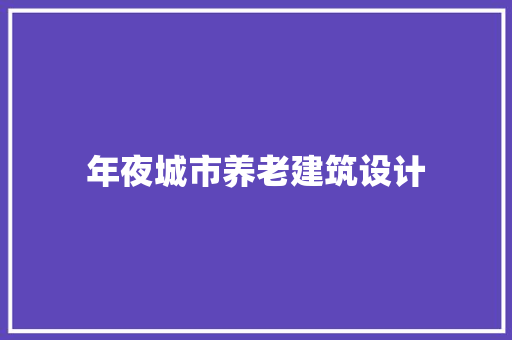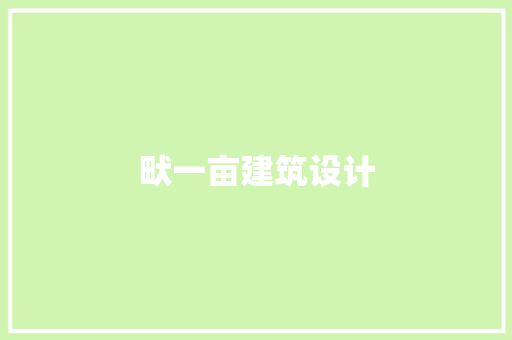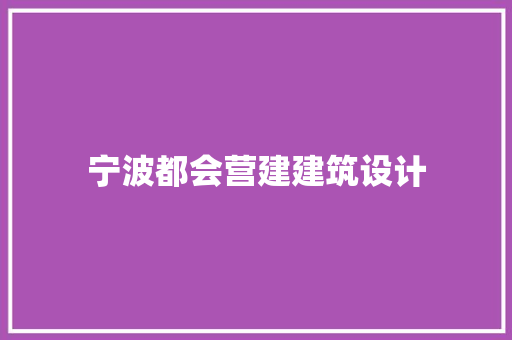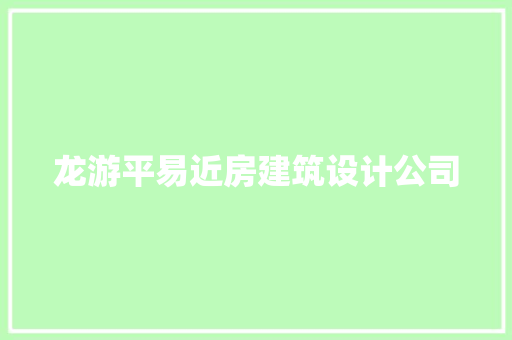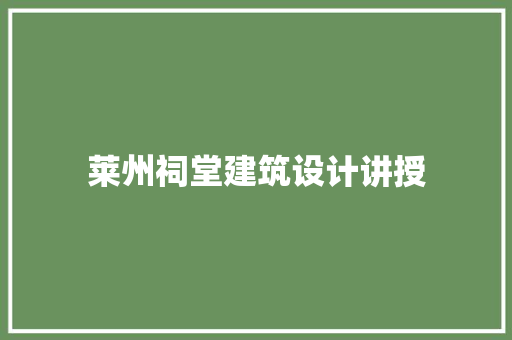曾经遍布黄河的渡口,如今大多都被桥梁取代。南长滩的渡口是末了存留的少数黄河渡口之一。| 拍照:谢佩霞
南长滩的日落要比银川早一个多小时的样子,盛夏时,贺兰山下的银川平原,大约到晚上9点才入夜。由于南长滩地处黑山峡峡谷间,傍晚7点,一轮斜阳就被北岸喷鼻香山的山尖挡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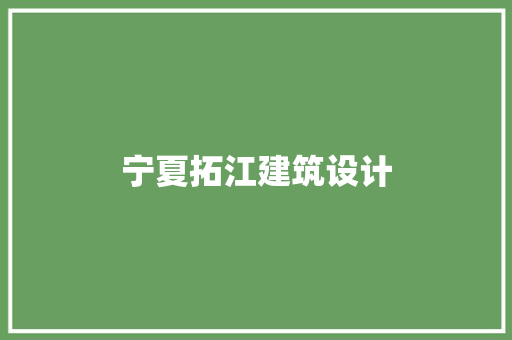
李进武在河边的渡船上喊话:“走不走?不走、我就回家啦!
要出山就得等来日诰日早上喽!
”行走拍摄黄河已经两年多,南长滩渡口的渡工李进武的一句喊话,让我们找到一个讲述黄河故事的切入点。
消逝的黄河渡口
我们曾到过那里,河水极浅,高原上的牛羊边吃着草,边排着队,在牧羊人的驱赶声中,就趟过了河。牧羊人则踩着河中的几块大石踏河而过,鞋都不会湿。
唯一的摆渡人
从北长滩去往南长滩,我们从宁夏绕到甘肃,又回到宁夏,终于在晚上7点遇上了“长滩一号”的末班船,河的对岸便是南长滩村落。
北长滩和南长滩,都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一个在黄河北岸,一个在南岸。南长滩渡口,是我们见到现存黄河渡口中少有的、保存如此无缺且原始的渡口。
“长滩一号”是摆渡人李进武的渡船。用粗体字呈现的“长滩一号”招牌支棱在船上最能干的位置——船舱顶上。乍一看,这名字起得有股舍我其谁的霸气。实际上,它只是如实交代情形。由于这个渡口,只此一条渡船。从来只有“长滩一号”,没有“长滩二号”。
待我们下了渡船,李进武跳上岸,把船在码头边固定好,这一天就算收工。朝七晚七,只要景象许可行船,他始终无休。他没有同事,也没有会开除他的老板。
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北男人,30岁往后的人生,可以用三条渡船为核心参照物来划分时段。
目前的“长滩一号”,是2017年新造的。造这条船,花了70多万元。渡船的票价也由他定:来回一趟,单人20元/人,摩托车30元/辆,五座小车60元/辆,七座小车80元/辆。村落里邻居乘船,则一律免费。
然而新渡船启用后的六年,李进武的收入并没达到预期。先是三年夏天这一带黄河泛滥,开不了船;接着又是三年疫情,来此的不雅观光客少了很多。吃摆渡这口饭,一要看天的神色,二要看人流量。
李进武已开了28年渡船,因长期日晒,他的皮肤看起来黑得发亮。他是这个渡口唯一的摆渡人。| 拍照:李颀拯
李进武的第二条渡船,也便是“长滩一号”的前身,购买于2011年。那条船小一些,一次能载2-3辆小车过河。再往前追溯,他买第一条渡船,是1996年的冬天。
那时他灵通,听说黄河上游甘肃的某个乡里在卖一条闲置的旧摆渡船,价格也让贰心动:三万元旁边。他想拿下这条船。他以为南长滩村落须要一条渡船,也暗暗以为自己命里会有一条船。
之以是记得是冬天买船,是由于他对拖船回村落的印象过于深刻。那时正值数九寒冬,黄河冻住了。四个人在又冷又滑的冰面上,被一条船搞得团团转,拖一阵,推一阵,再滑一阵。
这条渡船实在比李进武后来的两条船都小,载不了汽车(1996年村落里也没人买私家车),只能载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但对徒手拖船的人来说,已是庞然大物。几十千米的路程,他们折腾了九天九夜,才回到村落里。
李进武一说到感触特殊深的事,就自动把普通话切换成方言——只有方言能把他想说的意思淋漓尽致表达出来。虽不能完备听懂,但从他的长吁短叹中,我们捕捉到几个关键细节:
那是一年里最冷的日子,但他们热得汗如雨下,打着赤膊回的村落。因极度疲倦,他们的嘴全烂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回村落后,同行的一个伙伴恶狠狠地对他说:“老子这辈子就举措看成牛做马,都不会再跟你去拖船了!
”
就像许多故意义的奇迹都有一个艰巨卓绝的开头,从那往后,南长滩村落有了第一条拉索的渡船。在那之前,村落民过河都坐羊皮筏子,那是汉代就有的一种交通工具。
李进武则是南长滩渡口第一个当代意义上的摆渡人。那一年,他30岁。
至于他30岁以前的人生,就语焉不详了。
南长滩的渡船一次可载5辆汽车过河,在有这条渡船之前,村落民过河都坐羊皮筏子,那是汉代就有的的交通工具。| 拍照:谢佩霞
探求南长滩村落
去往南长滩的过程,是一段很难略过不表的路途。
我们先被导航带去几千米外的北长滩上滩村落。沿着网红景点中卫66号公路行驶30多千米,会看到一壁黄泥墙,上面刷着“涌泉村落”三个大字,题名的字迹已经斑驳,依稀能辨认出“山海情拍摄基地”几个字。
涌泉村落,是脱贫攻坚主题电视剧《山海情》里虚构的村落落。作为拍摄取景地之一的上滩村落则成了网红打卡地,为当地开拓旅游业引流。涌泉村落固然是杜撰的,上滩村落及这一带过往的穷苦、不宜居却是真实的。
这些村落落像直接从泥地上搓出来的,破败的房屋、围墙,外立面都糊着黄泥,村落道是土路,随便走几步就扬起滚滚黄尘。到处是土,但没什么人。能栽种的经济作物也很有限。换作你是《山海情》里的马喊水、马得福,你也想逃离这儿。
如今村落里的住户险些已搬空,若有动静,多数是游客在拍照。也有包着头巾的老妇围上来,说着很难听懂的方言。从她们手里捧的土特产大约猜到是在问:“要不要买点枣?核桃?梨干?”
她们是为数不多的留守者。
舆图显示3千米外的河对岸便是南长滩,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向当地牧羊老汉打听,他比划着说,前面山路太窄且塌方了,车过不去,须转头,绕道。结果这一绕,就绕了90多千米路,还须跨省——要穿过宁、甘交界地带。
去南长滩目前只此一条路,若不是由于扶贫工程的深入,可能连这样一条路也没有。
南长滩村落从属于中卫市喷鼻香山乡。喷鼻香山乡是宁夏中部干旱核心区,年均匀降水量只有180毫米。喷鼻香山并无花喷鼻香和鸟语,说是不毛之地并不夸年夜。穿过大片煤矿区、盐碱地,路越来越窄,许多路段只容一车通过,弯道又多,且都是急转弯。
新浇过的水泥路,总体平稳,偶尔有小段颠簸,也由于这一带属于土林地貌,山体地质不稳定,加上地下挖过煤,道路随意马虎开裂。群山连绵,我们在仿佛没有尽头的峡谷里不知拐了几百个弯,不禁感叹:壮丽是真壮丽,荒凉也是真荒凉。行驶近两小时,不见一人,亦看不到村落,有种说不出的寂寞。
“树!
那里有棵树!
”同行的拍照师溘然叫了起来。只见最远处的黄土坡顶上立着一棵树,在夕阳的逆光下,轮廓分外清晰。那是一棵枣树。行了十几千米才看到一棵大树,当然愉快。蜿蜒的山路,终于在那棵树所在的山脚下扫尾。
向右拐弯,面前豁然开阔,一条大河横在面前,黄河到了。不远处,停泊着一条渡船。至此,我们仍在黄河北岸。望向南岸,一派绿意盎然。最低处是河滩,白羊埋首于翠绿的草丛中;视线上移,是一大片坡度平缓的山坡,从山脚到山腰都是浓绿,有一大片树林;再往上,露出参差不齐的屋顶,可知是个村落。那便是我们要去的南长滩村落。
比拟刚才走过的路,面前的南长滩不仅是一片丰饶之地,也像一个奇迹。薄暮7点,一个黑得发亮的男人从渡船上站了起来,像是等了我们良久似的,他便是李进武。
村落里的党项后裔
坐渡船到了南长滩村落。码头东边有一座木头牌坊,横额上刻着两个西夏笔墨——全天下通达这种笔墨的,不超过十人。
牌坊背面刻着两个汉字:拓跋。
拓跋这个姓,一样平常先让人遐想到北魏皇族,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但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神秘的王朝,其皇族亦姓拓跋,那便是西夏。
据南长滩村落村落委会2023年8月供应的统计数据,目前全村落户籍人口为354户973人,常住人口122户208人。村落里紧张有拓、孟、张、马、李等十几个姓氏,个中姓拓的村落民占80%。
拓姓被认为是由拓跋姓发展而来,是证明该村落村落民可能是西夏党项族后裔的紧张证据。
南长滩村落的路牌,一壁是党项笔墨,另一壁则是汉字。| 拍照:谢佩霞
党项族是古代少数民族之一,原来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析支”(亦称“赐支”)之地,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线。
在与吐蕃等部族的战役中落败后,党项人内迁至黄土高原,以部落划分单位,逐渐形成党项八部,个中以拓跋氏最为壮大。
晚唐期间,党项拓跋氏因帮忙唐平蕃有功,唐僖宗奖励拓跋思恭,赐军号“定难军”,后封夏国公,赐姓李,拜夏州节度使。
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从11世纪前期至13世纪前期,西夏政权存在了190年。壮大期间,一度统一了中国西北地区,与宋、辽三足鼎立;后期,与金并立;终极,为蒙古大军所灭。
西夏王朝虽然灰飞烟灭,党项人却未被赶尽杀绝,他们向不同的地方亡命或迁徙。
有的去往华北,证据为今河北保定一带出土的“胜相幢”,上面用西夏文记录着上百个党项人的姓氏。有的去往西南,现在生活在四川甘孜地区的木雅人,曾建立过“西吴”政权,据历史学家考证,西吴便是西夏的延续,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信奉佛教的党项人去往青海方向,在湟水定居下来;有的乃至穿越了青藏高原,到达珠峰脚下,成了本日以“喜马拉雅山挑夫”有名天下的夏尔巴人。
20世纪80年代,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师长西席稽核了南长滩村落,综合考古发掘资料、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认为这个村落落是迄今创造的为数不多的古代党项人的鲜活载体。
“要说村落里有党项人的后裔,那本族谱倒是可以去看看。”李进武说的是南长滩村落拓氏重修于清朝咸丰年间的族谱,族谱在2013年又重新修订过,对从公元386年拓跋珪称王开始,到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乃至明清期间拓跋氏后裔的业绩,都有记录。
南长滩村落拓氏族谱。| 拍照:石宇清
末了的防线
村落里的老人们还总提及上个世纪的事,说那时村落庄对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拓氏宗庙,里面供有拓跋弘的灵位,能证明他们的根源,但后来不知怎么就被拆了,现在也说不清了。
南长滩村落在中卫最西头,间隔沙坡头城区91千米, 村落域面积195.4平方千米。黄河自甘肃进入宁夏,在喷鼻香山中穿行70千米,这一段被称为黑山峡。前面提到李进武把渡船拖回村落的路线,就属于黑山峡的一段。由于大山阻隔,出入不便,此地人迹罕至,十分宁静。
把光阴拉回到700多年前,一支姓拓跋的党项人在不安中开始迁徙,他们沿黄河往上游去,无意中途经南长滩,但见此地地皮肥沃,宜耕宜牧;既无人烟,又有黄河与群山为天然樊篱,不易被外人创造,适宜隐居;遂隐姓埋名,在此扎根——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片地皮要给党项人带来安全感,还得随意马虎防守。当初,拓跋姓党项人为躲避蒙古大军的追杀逃至南长滩,大概正是看中这里地形的易守难攻。
本日,从陆路开车来此尚如此困难,古代要骑马或步辇儿过来就更难了。黄河水由南往北穿越黑山峡,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善于骑射的蒙古军要通过水路到达这里,更是难上加难。
对付要戒备外敌的党项人来说,南长滩天然具备两道防线:一是高山,可以高高在上察看敌情;二因此黄河为天堑的渡口。
千百年来,宁夏中卫一带的人都很熟习羊皮筏子,很多人都会制作。如今,南长滩只存有一只废弃的羊皮筏,它悄悄地靠在一处旧房背后。| 拍照:李颀拯
南长滩有一段古长城和一座烽火台,烽燧傲然耸立在山岗上,经数百年风雨侵蚀,望之与黑山峡十全十美。“古烽台”所在的高山,宋代时原称烽台山,后来俗称“丰台山”。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黄河黑山峡长城始筑于秦始皇先祖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进行修建。汉武帝时,边陲西拓后,这里就不再是边关了。
我们在南长滩村落创造一件故意思的事,便是在许多村落民家的院子里,都能清楚地看到对岸山顶上的那棵枣树,也便是我们来时看到的那棵树。61岁的民宿房东拓江说,那可不是普通树,听爷爷那一辈老人说,那是棵旗子暗记树。
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带确有匪患。民国期间,喷鼻香山地区的“山大王”冯建忠,曾带领一批人马驻扎在对岸的北长滩,利用黄河天险打劫过往商贸筏子。
一旦有情形,在枣树边土墩里值班的村落民可以在枣树上挂不同颜色的旌旗发出预警,让村落民提前做好准备或撤离。“由此可以想象,或许当年拓跋氏就如此戒备蒙古人,然后安下家来。”拓江曾和来村落里调研的历史学专家互换过这个问题。专家则认为此不雅观点还“须要考古成果进一步证明”。
本日,枣树边的土墩已经没有了,烽火台也只剩残垣断壁,但旗子暗记树和渡口还在。
无常的水位
历史上的南长滩曾尽享水运之便。千百年来,宁夏中卫一带的人都很熟习羊皮筏子,很多人都会制作。自重约50千克的筏子,能运载约1吨的货色和人。
水路是唯一出口,但在没李进武的渡船之前,只能靠羊皮筏。
南长滩村落依山而建,住在这里,首先要习气爬山。不难创造,村落民住宅都集中在山顶,至少也建在山腰以上的高位——这样设计不但为看清对岸的枣树,也和母亲河变革无常的水位有关。
每天守着渡船的李进武,没有错过任何一场山洪暴发。他向我们描述过印象最深的一场大水,曾把他困在北岸的山坡上,50多天回不了家。家人都在南岸,也过不来。那一个多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细节不堪回顾。
但对67岁的村落民陈建义来说,变革无常的黄河水,却是他的乐趣源泉。喜好奇石的陈建义创造,每当有大水漫过渡口的浅滩,就会有很多新的俊秀石头从上游冲下来,滑润光亮,乃至透着玉的样子容貌。
后来,渡口通船,村落里游客多了,他家开起田舍乐。一天,有个客人一眼就看上了他家的石头,问他“卖不卖?”这之后,石头也成了买卖。每次有客人来消费,他就赠予奇石。
全村落登记在册的村落庄民宿有15家。每逢梨花节,游客多得接待不过来,家家户户客串民宿且都满房。宰羊烹羊,处处飘喷鼻香。该村落村落民的人均收入,排在宁夏屯子人均收入中上水平。
南长滩的羊肉品质好在宁夏是出了名的,养羊是村落民的紧张收入来源,大部分村落民都养羊,全村落共有 26000 多只羊。每逢梨花节,宰羊烹羊,处处飘喷鼻香。| 拍照:吴旭芳
但疫情三年,对村落庄旅游的打击很大,村落里好几家田舍乐都关了。等不了转机到来的人,只能自寻出路。早上7点,村落里的拓守财就坐第一班渡船出村落去了,他去中卫的沙坡头看一间门面房,打算在那儿开个小饭店。实在几年前就有朋友劝他离开南长滩,当时他还下不了决心。
今年,听说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进入了环评阶段,地质丈量队也频频涌如今周边一带。拓守财意识到,不得不重新考虑往后的日子了。
黑山峡是黄河上游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的末了一个峡谷段。2023年5月,甘、宁两省区在开拓方案上达成共识,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进入可行性研究报告体例阶段。同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官网上对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示。
早在4月,宁、甘两地公民政府官网上就分别发布了“关于禁止在黄河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占地和淹没区新增培植项目及迁入人口”的通知布告。从官方公布的信息可知,“工程正常蓄水位1380米,占地涉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喷鼻香山、常乐、迎水桥3个州里的上游、黄泉、孟家湾、上滩、梁水源、下滩和南长滩7个行政村落及淹没区”。
南长滩村落,正是在工程占地或淹没区范围内。
黄河水位的起起伏伏是永恒的。南长滩村落的人在浮浮沉沉中守在原地,努力把小日子过得踏实。只是这一次,面对未来的新水位,他们将再一次迁徙。
由于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就认定村落民都很守旧,畏惧变革,是一种常见的刻板印象。南长滩的人,很多时候都拥抱变革。
如今,在村落里小店买东西,和去城里商店没什么两样,都可以扫二维码支付,微信、支付宝,都行。对新事物,村落民们从来不排斥,便是跟进的速率,总比表面的天下慢几拍。
村落里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少,孩子也越来越少。几年前,村落里的学校生源不敷,也关了。“年轻人回来干什么,随着我开渡船吗?”李进武自我解嘲说。
风陵渡的孩子们都知道村落里有渡口,但谁也没见过渡船。由于自他们出生时,村落里就已经有了桥。| 拍照:顾春序
末了的黄河渡口
村落里要说变革小的,还是那个渡口。
21岁的周学辉正在银川上大学,他认为,村落里该当建一座桥。他回顾,小时候假期回来时,他最担心的便是黄河涨水,一旦涨水,船就不能开;其余,一定赶在入夜前到达,否则也无船过河。
像他这样的“造桥派”能找到的参照物很多。1970年12月,宁夏第一座黄河公路大桥——叶盛黄河大桥建成通车;1993年3月,宁夏第一座黄河铁路大桥——宝中铁路黄河大桥通车。此后几十年,宁夏境内黄河上相继架起20多座大桥,均匀每十几千米就有一座。
但南长滩村落也有很多人反对建桥。对村落民们来说,无论各家的生活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便是与渡口相存相依。
黄河边,一个孩子顶着块沙发垫跑回家。这被人摈弃的垫子是从上游冲到古渡边的,孩子想放在院里,和小朋友们做游戏用。在黄河边,村落民时时时能捡到上游冲下的东西。| 拍照:顾春序
如今定居在中卫的拓兆柏,原来是南长滩村落小学校长,在这所小学事情了36年。他回顾南长滩,第一个就会提及渡口,由于孩子们进进出出都要过黄河,每次学校的安全教诲,渡口是第一个要强调的。
在没有拉索的渡船前,孩子们每次坐羊皮筏,都是一次冒险。后来,孩子们终年夜,要去表面求学了,拓校长就站在渡口,送走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再后来,渡口的对岸便会传来一个又一个好:谁家孩子考上重高了,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
拓守财认为交通不便始终是个问题。前些年,他盖屋子,拉砖、拉水泥,从河的那边运过来,本钱就增加一倍。冬天烧煤,煤矿就在河对面的翠柳沟里,一吨煤加上运费到家里价钱就翻了一番。
夜里,喝了点酒,拓守财开始说对岸的北长滩,那边的村落民原来日子过得不如南长滩,他们乃至到2006年底才结束点石油灯的历史。
2007年,拓守财到过北长滩,觉得天下溘然寂静了,由于移动网络没有覆盖,手机没有旗子暗记。他看到一只耐不住寂寞的毛驴仰头“昂昂昂”的长叫几声,甘于寂寞的老牛却围着磨盘转了一圈又一圈。
2023年,再去北长滩,中卫66号公路是必经之地。通路后北长滩一带的年轻人陆续外出,或打工或做生意,许多人都在沙坡头安了家。去沙坡头,也写在了拓守财的日程表上。
老一代口耳相传的故事,村落民并没有那么在意,当务之急还是过好本日和来日诰日。| 拍照:谢佩霞
什么叫发展?
在李进武朴素的认知里,便是先有一条小渡船,努力事情,赚到了钱,换条大点的渡船,然后连续努力,换更大的船。他成为摆渡人之后的生活轨迹正是如此,28年,买过3条渡船,一条比一条大,渐入佳境。
只是他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性:发展,也可能是跨上一大步,让许多事直接翻篇。比如,渡口就可能由于水利工程在一夜之间消逝,那时,有没有船、有什么样的船,都不主要了。
在格林童话《妖怪的三根金发》中,有个舟子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一贯在为人摆渡,总是脱不开身去做其他事?”妖怪回答:“把船篙塞给渡客,让他取代你的位置,不就可以脱身了吗?”
不过李进武既不看童话,也不须要妖怪辅导。他今年58岁,距法定退休年事还有两年。渡口有没有人来接班,或者他会不会在退休前先失落业,在他看来,问题都不大。
两年而已,毕竟不像已经由去的28年那样漫长。李进武非常笃定的一件事是,无论南长滩的村落民何时迁居,他一定是末了离开的人。
由于,他要用渡船把所有人先送到对岸。
位于甘肃的莲花古渡,别号黄河下渡,在历史上曾有主要浸染。在刘家峡水库蓄水后,老渡口已沉入水底。| 拍照:谢佩霞
作者:李颀拯,纪实拍照师,著有《怒海谋生》,9次得到“金镜头”拍照奖项。经由 3年韶光准备,他在2021年组建VOIRFOTO拍照团队,启动“黄河操持”。(原文刊于《中原地理》杂志10月刊)
伸出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