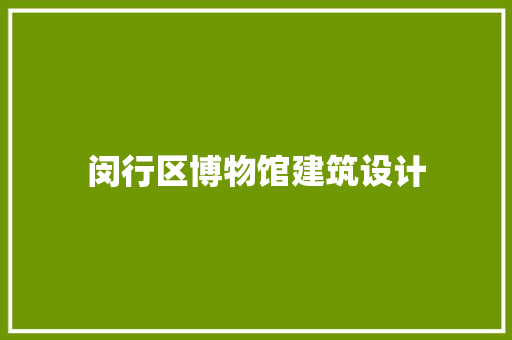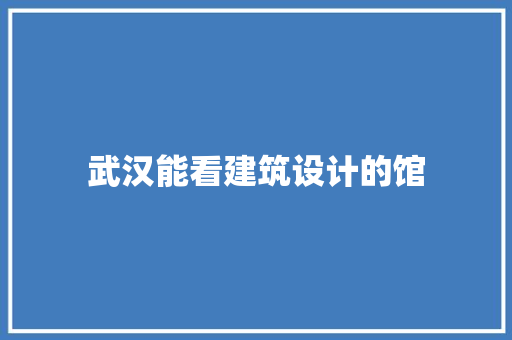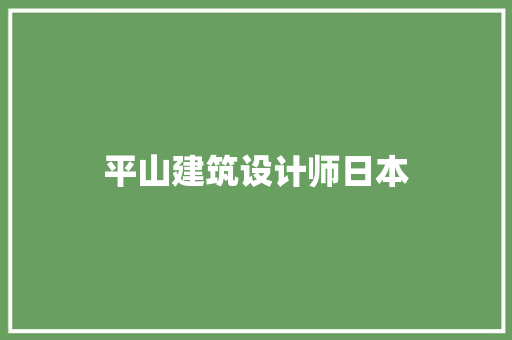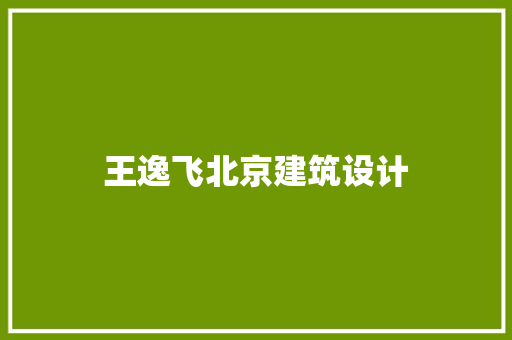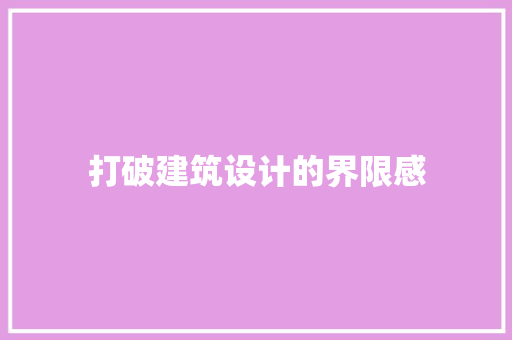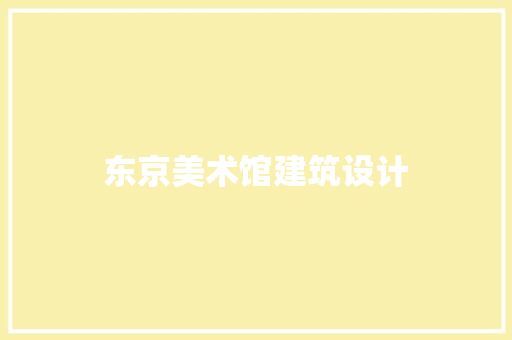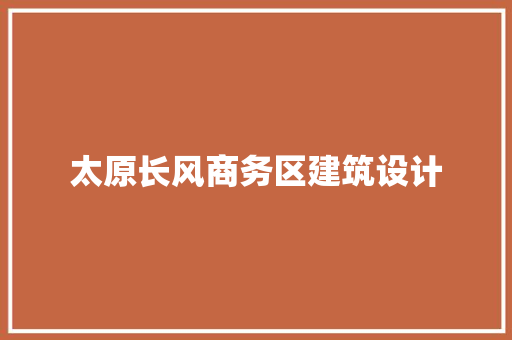菲美特金属铸造厂是位于通州城关镇的老厂子。20多年来,这些铸造钢铁的坚固厂房矗立在京杭大运河边,留下了一段辉煌的工业时期。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央确立,这里被方案为了副中央CBD核心商务区,而这个老厂子,在这种开拓的浪潮中,是被毁灭,还是能够延续一些文化的基因,大概是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央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城市文化副中央的关键。在成功运作了几个老工业遗产开拓项目后,普罗建筑被约请为这个运河边的老厂区策划一个新的转变,让这里成为北京的“西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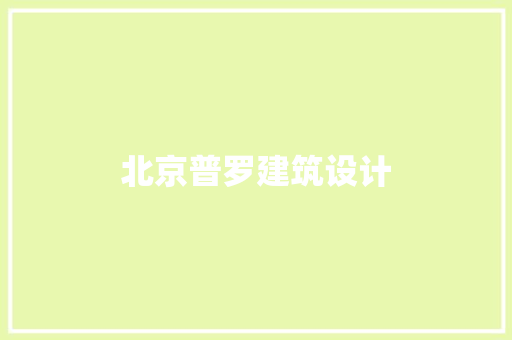
将通州废弃工厂改造成“一座没有大门的艺术馆” ©常可
改造前基地位置(左);美术馆原始基地-废弃的工厂宿舍区(右) ©常可
在多番磋商过后,全体工厂终极被策划为一个以办公为主的艺术型创意家当园区。但是,如何处理河岸边最近的一片工厂生活配套区,成为一个难题。这片由四座一层条形单元宿舍房以及园区小食堂组成的区域,建筑面积小,分散。由于改造建筑轮廓线不能变动,这样的平面布局作为办公险些很难以利用。那么不作为办公,是否可以引入一座公共的美术馆呢?把全体区域统合起来,使其成为“一座没有大门的艺术馆”,让文化和艺术成为全体家当园区的引擎,同时,给"大众一个河边的文化社交空间? 这是一个让人愉快的想法!
最核心的功能定义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逐步解读园地,使其与我们的功能相契合,匹配出一个新生的建筑体,乃至是我们心目中空想的美术馆原型建筑。
改造后的创意园区与美术馆 ©夏至
一个河边的文化社交空间 ©普罗建筑
加法到减法的转换
从“建筑群”到“一个建筑”,“外部”展场如何成为“内部”艺术洞穴。
韶光的洞口 ©孙海霆
“切削出”的隧道 ©常可
风光水在这里交汇 ©孙海霆
原来园地等分散的建筑体量只能称之为“展厅群”,却无法成为“一座美术馆”。如果我们不将这些建筑体算作体量的“凑集“,而将体量之间的“空”的部分算作是在一个整体上的“挖出”,也便是将加法转化为减法,我们就得到一个“整体”的美术馆。通过一系列的“挖出”操作,形成一系列凹陷的洞穴。这些“洞穴”将原来展厅群的外部空间,本色上转化为完全美术馆的内部空间。
“洞穴”组合成了贯穿整体的人工“隧道”。“隧道”被每块巨石展厅所围合,韶光,空间,风,声音,水都在这里交汇。这种犹如业走在构造内部的感想熏染,唤起了艺术的原始冲动,形成了身体层面的艺术场域。韶光在这里仿佛不再是单一线性的元素,而成了一种循环。
从加法到减法-空间天生图解 ©普罗建筑
建筑模型 ©常可
一层建筑平面图 ©普罗建筑
朝向广场的水平建筑体 ©孙海霆
改造后的建筑体 ©常可
朝向北侧的入口 ©孙海霆
光影布局的引力场 ©孙海霆
巨石走廊 ©孙海霆
原来静置的排屋,被组织成一组相互锚固的巨石与石洞。这些交错的“隧道”成为周边城市空间的交汇点,也构成了美术馆的室外公共迷宫。迷宫空间这种古老的空间体验的探索感是一样平常的功能效率空间所无法比拟的。通过构建光影“迷宫”空间,传统封闭的美术馆空间就成为了开放式的户外“公共艺术场域”,其展览与展品,与展示办法,与参不雅观互动的游客都更紧密的有所关联,而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精美建筑体。一个鲜活的美术馆由此出身。
建筑剖面示意 ©普罗建筑
光影布局的引力场 ©孙海霆
水上悬浮的迷宫 ©常可
隧道中的室外展区 ©孙海霆
将“外部空间”转化为“内部空间” ©常可
为了更好的表示巨石迷宫的光芒与岁月感,我们选择了沉喷鼻香米黄砂岩作为外墙的主材,并在分隔上做了大量的研究比拟,并做了一比一的真实比例样墙,以使得末了美术馆呈现一种最大化的“完型”感。地面为了与之匹配映衬,我们也用了芝麻岩并做了相应的模数分隔处理。
沉喷鼻香米黄石材对光芒的奇妙接管与反射 ©孙海霆
地面花岗岩石材与墙面石材的领悟 ©孙海霆
水系、架高层、空中廊与流动的人流 – 被吸纳的风景
运河美术馆实在很分外,它虽然体量很小,却并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单元,它既是园区内部的一部分,又是园区开放的窗口,同时又由于可以和外部隔岸相望,因此美术馆的定位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开放空间与箱庭空间的领悟,是外部与内部视角的相互转化。
二层平台与被吸纳的风景 ©孙海霆
二层平台的明暗创造空间深度 ©孙海霆
光芒对付空间的“切削” ©孙海霆
再回到场地本身,虽然这部分体量依旧矗立在园区围墙内,但是它特有的地形高差,使得美术馆一贯和外界的运河堤岸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隔(物理位置上的分隔)与不隔(视线上的沟通)的关系。因此在靠近运河的一侧,我们设计了架高半层的外廊,与地面的石洞隧道遥相呼应。在这个架高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超越园区的围墙与墙外的车流人流共享运河的美景,吸纳其成为美术馆的外部环境。同时,这些架高的连廊也是将几个独立展厅串联成一条完全又丰富的参不雅观流线的主要一环。
与运河关系剖面大样图 ©普罗建筑
架高层带来穿透的风景 ©孙海霆
多重的穿透 ©常可
多重交汇的廊道 ©孙海霆
沉思之廊 ©常可
多重交汇的廊道 ©常可
我们为每条展馆都设计了不同的水系,水的流动也在悄悄勾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在第三条展厅的后部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无边池塘,在这里建筑与围墙,弧形的池塘一起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广场空间。地面一层,下沉层,架高层,这三个空间层次让单层的美术馆得到了垂直向的立体游览体验。在展馆内,通过低窗的设计,建筑间的水系也成为展馆内的展示元素,使室内外展区模糊了边界。
水系穿透形成勾留空间 ©常可
勾留空间 ©孙海霆
弧形池塘连接连接两边隧道 ©孙海霆
室外成为展窗 ©普罗建筑
水系成为展品 ©普罗建筑
除了美术馆自己内部的设置和连接。还有一条贯穿全体园区的“空中之廊”,这条流线从园区中心办公区的二层廊桥超过而出,再下到地面进入到美术馆的入口售票厅。因此介由不同的角度进入美术馆内会看到不同的景不雅观,体验到不同的水,与地面,与墙面,与参不雅观的人流的各类不同关系。这些不同自然是十分主要又分外的体验,也是我们对传统中国园林的一种转译考试测验。同时,这些外部联结将人不断引入美术馆的“公共艺术场域”中,使人的活动本身成为了展品。
通向的美术馆的公共艺术廊道(左) ;流线示意图 (右) ©普罗建筑
空中之廊模型 ©常可
空中之梯进入美术馆 ©孙海霆
空中之廊与地面下沉悬浮入口 ©孙海霆
空中之梯进入美术馆 ©夏至
空中之廊入口 ©夏至
空中之梯进入美术馆 ©常可
下沉悬浮入口的光井 ©常可
生活是没有大门的艺术
我们一贯认为,改造是一个出发点,一种路子。鲜活而纯粹的艺术不应该被其手段所束缚,而该当导向更多义的建构。如何回应建筑的场所,如何创造更开放的生活,是我们设计磋商的重点。我们相信园地本身就有它诉说故事的力量,只是悄悄等待着能与它们互换的设计师的涌现。而运河美术馆的力量就在于韶光与场所的对话。
通过对原始园地空间逻辑的继续与转译,我们将分散的“展馆群”构建成给予人身体包裹性的“美术馆整体构造”,同时,将美术馆彻底变成了生活中的街道空间。这解释,未来的艺术空间将更关注于回归人原始内在的体验与感想熏染,而不仅仅勾留于对艺术品本身的展示。通过运河美术馆的项目可以看到,当艺术与生活相交融,艺术就不会存在大门。
光井 ©常可
美术馆北侧入口 ©孙海霆
没有大门的艺术馆 ©常可
改造施工过程 ©普罗建筑
平面图 ©普罗建筑
立面图 ©普罗建筑
墙身节点详图 ©普罗建筑
项目地点:北京市通州区
项目性子:美术馆
设计周期: 2018.8-2018.10
建造周期:2019.3-2019.11
建筑面积:1900.57平方米
业主单位:通州新潞文创园
设计单位:普罗建筑 officePROJECT
主持设计师:常可、李汶翰、刘敏杰
设计团队:姜宏辉、张昊、赵建伟、冯攀遨、袁博,林旺铭,陈斌斌,魏斌(驻场),王佳桐,扈诗雨,吴喷鼻香丹
拍照:孙海霆、夏至,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