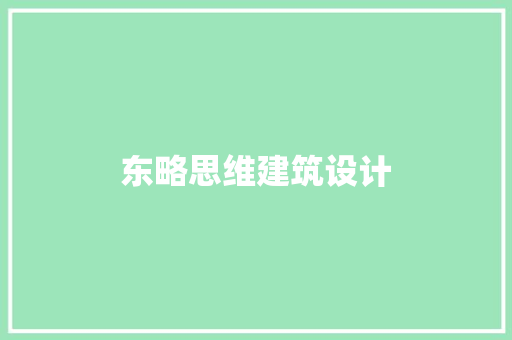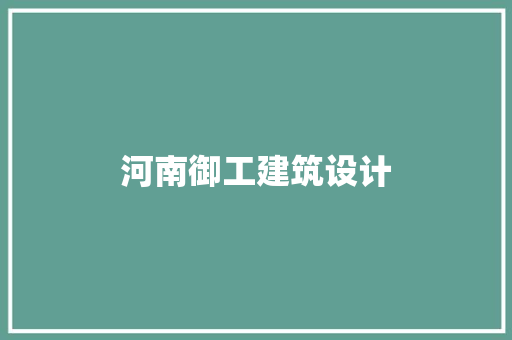这个小字"铁胡"的哥儿们虽然出身粟特族,但几代人效命中原王朝,早已是真正的中国人了。当契丹异族大举南下,企图牧马中原之际,石晋不仅屈己听命,还以儿天子自许,不惜残民供奉。铁胡哥虽受石敬瑭特赐,但却不耻臣戎自贱,更不愿平生易近受虐,疾呼"诎中国以尊戎狄,此万世之耻也",千载之下,犹有余响。铁胡哥毅然举兵反晋,虽败犹荣。他便是出身粟特,却有一颗中国心的安重荣。
孔子说:"戎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又说,"戎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这两句话可谓道尽了中国文化的原谅性和前辈性。五千年来,中华文化犹如灯塔一样,驱散野蛮,教养文明,哪怕再凶暴的戎狄也会被中华文化所同化。本文猪脚便是一位拥有一颗中国心的粟特族将领安重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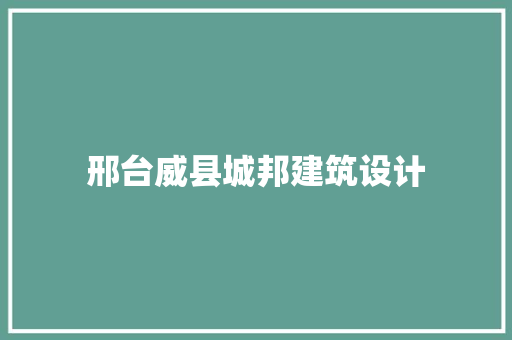
小字铁胡的安重荣是朔州人,生年不详。不过他的生年不详可能是史家漏记,由于这哥儿们出身并非平凡百姓之家,而是累世勋阀,该当不会连个生日都不记得吧。安重荣的祖父安从义曾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父亲安全出任振武军(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马步军都指挥使。
安重荣从小随着父亲生活在振武军营里,属于部队大院里终年夜的野孩子,不仅膂力过人,而且长于骑射,一看便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棒小伙儿。
安重荣不是汉人,他出自粟特族。读者大大可能知道,粟特族是古代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商业民族。
粟特族在中国古籍中又被称作昭武九姓,听说,粟特族的先人出自昭武(今甘肃张掖)城的九大部落,后被匈奴攻击逼迫,散入中亚建立多少城邦国家,如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等,个中以康国为首。
粟特人居住的中亚地区,位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粟特人靠路吃路,在商言商,养成了冠绝天下的商业特长(史载粟特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他们不辞辛劳地将中原的丝绸贩卖至欧洲,又将西域的美玉、玛瑙、珍珠地贩入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粟特人中多有豪商殷商,同时,由于他们走南闯北眼界开阔,也偶尔会冒出一两个野心家来,如安禄山、史思明都出自粟特。至于二人麾下的将帅,也有不少是粟特人,不过,他们的家族在中原定居数以百年,早已汉化,没有了安史二人那么大的野心,充其量只想做一个拥兵自重的藩镇。
安重荣的家族来自古安国,虽然也姓安,可与安禄山是同姓各家,一贯规规矩矩地在中原王朝的治下为官做宰,早已拥有了一颗不变的中国心。
年夜公元933年前,军营里终年夜的孩子安重荣早已接过了父亲手里的钢枪,发展为振武军巡边指挥使。不过,边陲地区,汉厮混居,民风彪悍,历来是多事之地,作为巡边指挥使,难免会卷入个中,结果安重荣一欠妥心就变成了犯罪分子,差一点还丢了脑袋。
关键时候,安重荣的老娘挺身而出,遑急火燎地奔赴洛阳,托关系找后门,诣阙申告,终于冲动了李嗣源,特旨赦免了安重荣。虽然,笔者查不到安重荣到底犯了啥罪,但这种猛男每每性情冲动,干事不经大脑,幸好有个老娘如定海神针般护佑着他。但是,老娘护得了一次,护不了终生啊。安重荣冲动的性情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振武军说得好听点儿是朝廷边军,说得不好听便是边缘化的军队,在这个军头里混,恐怕一辈子也很难出将入相。
性情冲动的安重荣是抱着安邦定国的空想从军的,他一贯在不雅观望中原王朝的变局,特殊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大祸之后,他更加渴望能够在中国的舞台上展露头脚。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就在中原王朝经由李嗣源的细心打理,正在向好发展确当口,老天爷夺走了李嗣源的阳寿。李嗣源刚去世,他的儿子、养子、半子就打得不可开交。
作为后唐末帝李从珂最劲敌手的石敬瑭,于公元935年在太原起兵。不过,初树反旗的石敬瑭兵力不敷,特殊是缺少具有攻击性的骑兵。
对此,石敬瑭派人到多个藩镇进行联结,大开空缺支票拉人。在振武军呆得有些职业倦怠的安重荣,就被石敬瑭的人事代理一番忽悠,决定率领部下1000骑,离开振武赶赴太原,投入石敬瑭的麾下二次创业。
一番口试之后,石敬瑭对安重荣比较满意,又对他亲口许下重诺。安重荣以为老石这个人不错,就安下心来,在河东军干得风生水起。
之后,石敬瑭如愿登上了帝座,建了后晋政权。他也没有辜负安重荣这员猛将,命其担当治镇州(今河北正定)的成德军节度使。
成德军是中唐以来最牛掰的河朔三镇之一,承担着防备契丹、巩卫北疆的重任,其镇兵不仅人数浩瀚,而且战斗力极强,石敬瑭把如此主要的军镇交给安重荣,足见对他的倚重。
安重荣由一个边镇将领晋级为大镇藩帅,可谓青云直上,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安邦治民的夙愿了。
通达文吏的不屈灵魂
安重荣虽然是粟特族军人出身,但却绝对不是一个只知打打杀杀的大老粗,他的身上依然流淌着粟特人长于经营的血脉,用书上的话说便是通达文吏之事。
精明干练、处事果决的安重荣,留神治道,勤于政务,每遇诉讼案件,必亲临大堂明辩曲直,坚持依法裁决。至于百姓徭役、课税、仓库耗羡等事关民生的大事,他更是事必躬亲,武断堵住胥吏营私的漏洞,虽然为此得罪不少地头蛇,但却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不少实惠。
总之,在安重荣重在安民政策的带动下,成德军高下风气焕然一新,昔日那些威风八面的官僚和衙役们,再不敢贪赃枉法,胡作非为,镇州百姓终于可以过上几天好日子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众所周知,石敬瑭的上位是依赖契丹扶持的。契丹人本着无利不起早的原则拥立石敬瑭,收成远远超过了支出,他们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幽云十六州,霸占了威压中原的形胜之地,而且还当上了石敬瑭的干佬儿,可以变着花样索要干儿子的孝敬。
对此,安重荣是武断反对的。他曾经上表直斥"诎中国以尊戎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之耻也"。安重荣的表章引起了不少朝臣的共鸣,却被固执己见的石敬瑭置之不理。
诚笃说,作为粟特人的安重荣和作为沙陀人的石敬瑭是有相同之处的,他们都不是汉人,只是汉化已深的中国人,而且在他们心中都会认可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也都明白自己与契丹异族不是一起人。所不同的是,安重荣有一颗不甘臣伏的中国心,石敬瑭则只有一颗甘当异族孝子贤孙的奴才心,这就决定了二者对待契丹异族大相径庭的态度。
契丹认为后晋这个儿天子是自己一手扶持的,那么自己就可以毫无压力地对后晋予取予求。因此,契丹天子和重臣们总是变着花样地向石敬瑭索要供奉。石敬瑭本着将儿子做到底的武断决心,总是无原则地知足契丹权贵的各种无理哀求,竭中华之物力,结契丹之欢心。
这让安重荣非常光火,决定脱手惩处不可一世的契丹青鸟使。当契丹青鸟使途经镇州时,一旦被安重荣见到,他不仅不会远接高迎,反而对青鸟使箕踞谩骂,借以打击契丹青鸟使的嚣张气焰。如果青鸟使非要和他较劲,他恰好可以借机杀之。一来二去,搞得契丹青鸟使都不敢正视镇州,只好跑去向石敬瑭埋怨。
这还不算,自从契丹崛起于北疆之后,不仅对中原汉人构成威胁,对付生活在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如吐谷浑、沙陀、党项等同样苛捐杂税,肆意劫掠,还逼迫他们自带干粮和武器作为奴隶军,南下侵扰中原。这些部族本来在北方生活得好好的,现在却要为别人打仗,胜了好处都归契丹,败了自己还要承受巨大伤亡,如此费力不谄媚,这些部族自然不肯意为契丹人火中取栗。于是,他们纷纭扶老携幼逃往中原,希望得到中原王朝的庇护。至于那些生活在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更是不满契丹的残暴,纷纭逼上梁山。比如原朔州节度使赵崇就联合城中旧部杀掉契丹人委任的伪节度使刘山,企盼回到中原王朝的怀抱。这些失落陷契丹的部族纷纭致书后晋朝廷,强烈哀求后晋顺乎民情,乘势发兵,击败契丹,保护塞上各族。
安重荣对付朔州老乡的义举感同身受,总是费尽心机地给予支持,乃至他还招揽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南归。不仅如此,他为了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还将自己当年的奏章附上各族请愿书,传示后晋大臣和四方藩镇,颇得民气。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得知此事,立即派人责令石敬瑭,将那些脱辽者押送回契丹,同时,哀求石敬瑭严厉惩罚那些保护脱辽者的后晋官吏。石敬瑭对这些无理至极的哀求逐一照办,誓将儿天子做到极致。
对此,安重荣朝气难平。安重荣原来还以为石敬瑭认契丹做干佬儿不过是权宜之计,一俟中原王朝稳定之后,石敬瑭一定会幡然悔悟。哪知道历经风雨才登上宝座后的石敬瑭早已是"苍然老贼,皓首匹夫",只要能够担保自己皇位不失落,统统国家利益与名誉皆可出卖。这让安重荣失落望至极,也武断了造反的决心。
曾亲自经历过后唐后晋政权更迭的安重荣一语道出彼时皇位争夺赛的真谛"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当为之"!
这与当年陈胜在大泽乡喊出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异曲同工,都是催人造反的战斗口号。
安重荣对石敬瑭彻底失落望了,正当壮年的他不甘心像个孙子似地拜倒在异族的铁蹄之下,他要为那些惨遭契丹压迫的各族百姓张目,也要追求更高的民气抱负,于是,造反成了他的不二选择。
此时的石敬瑭也没闲着,他一手捧着契丹干佬儿的诏书,一手掂量着如何对付安重荣。
垂垂老矣的石敬瑭知道皇位来之不易,以是他断然不敢违拗给他戴上皇冠的契丹,但是,他也不想就此和手握重兵且颇得民心的安重荣翻脸。他只想安安生生地做几年天子,可是哪想到咋就这么难呢?无奈之下,他只好一壁传出诏书,叮嘱安重荣对契丹依令而行,不论碰着何种情形,都需恪守成约,勤谨事奉;一壁派出殿前供奉官张澄率兵2000,将已南下至并、镇、忻、代(在今山西中部和河北西部一带)各州的部族百姓驱逐回原地。可是,这些百姓好不容易逃离契丹魔爪,如何乐意回去受罪?于是,他们都相约来到成德军治所,向安重荣请愿,希望能够得到安的庇护。
此时的安重荣已经心生反意,对付这些无家可归的部族百姓,急速汰弱留强,编成部伍,进行演习,准备发难。对付老弱,他也没有放弃,而是尽可能地妥善安置,一韶光,百姓归者如潮,谁也不再搭理石敬瑭的诏旨。
这下,石敬瑭坐不住了,他知道安重荣这是准备拷贝自己的夺位的成功范例啊。这怎么行呢?一想到那个犹如自己年轻时一样,文武双全的猛男坐拥大镇,统帅雄兵,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样子,石敬瑭做梦都会吓醒。于是,他只好拿出自己当年笑傲疆场的那股猛劲,亲自坐镇邺都(今河北大名),调集各路藩镇准备讨伐安重荣。同时,他给安重荣连下十道诏书,希望安重荣屈服前旨,和他一样做一个认贼作父的乖宝宝。
安重荣见石敬瑭齐心专心卖国求荣,对后晋再不抱任何希望,决心与昔日老板分道扬镳。
公元941年,安重荣乘石敬瑭移驾邺都之际,致书治襄州(今湖北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安"字,希望安从进乘京城空虚之际北进,与成德军南北夹击,共图大事。
这里顺带说一下,二安虽然同姓,但安重荣是粟特人,安从进是沙陀索葛部人,二人还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同姓人。不过,沙陀与粟特同属印欧语系的白种人,且长期通婚,至五代时差异已经不大,再加上安从进算是安重荣起身时的振武军老乡,二人虽不同族,但却交心已久。
接到安从进起兵的,安重荣立即率部相应。此时,旱、蝗磨难遍及河北,百姓本就困苦不堪。不过,大家一听安重荣是要举兵抗击契丹,急速忘乎以是地追随安大哥起兵。安重荣的义军迅速膨胀到数万之众。
安重荣带着他的义军没有北向幽云,而是扑向了邺都。对此,安重荣阐明道,先除国贼,再灭外寇。义军早就对石敬瑭当儿天子辱国害民一事切齿痛恨,听说安重荣要兵谏石敬瑭,自然双手附和。
安重荣的义军行至宗城(今河北威县),与石敬瑭派出的弹压大军不期而遇。狭路相逢勇者胜,安重荣和石敬瑭的好妹夫杜重威杀在一起。
杜重威是个没节操的二货,不过,此时的他率领的是后晋的精锐,再加上石敬瑭在后面坐镇,他可不敢有啥二心,只能冒死去世战。
韶光一长,安重荣大军吃不住劲了,一呼百应的义军毕竟不如职业军人的抗打击能力强。眼看着义军形势不利,素与安重荣不睦的成德军将领赵彦之溘然倒戈,冲出义军阵营,向晋军大队玩命奔去。这下,安重荣始料未及,义军顿时阵脚大乱,两万余将士尽皆溃散,大部分被冻饿而去世,或被得理不饶人的杜重威杀去世。
善骑射的安重荣倒也不暗昧,带着十余骑亲将在乱军冲突而出,逃入镇州。杜重威随即率得胜之兵重重围住了城高池深的镇州。
安重荣虽然身陷重围,却不甘束手就缚,而且,他知道自己同时得罪了两大强敌,无论是契丹还是后晋都不会放过他。既然如此,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奴颜媚敌,苟活一世?
安重荣动员城中百姓共同御敌。镇州百姓一则感念安重荣素日恩德,二则对暴敛媚敌的后晋朝廷素无好感,于是,大家强忍宗城之败亡夫丧子之痛,当仁不让地在外无援兵、内缺粮草的情形下奋力去世战,拒不平膝降服佩服,给予晋军巨大的杀伤。
不过,任何坚城也挡不住内部的蛀虫。杜重威见强攻不成,就大撒银弹收买城中将校,结果一个家伙见钱眼开,从城西水碾门放晋军入城。守城军民虽拼力阻挡,终因寡不敌众,两万余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安重荣又一次突出了重围,率领仅存的数百名吐谷浑骑兵退入牙城,准备与晋军做末了的搏杀。
公元942年正月的一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早已粮尽多时的安重荣再也拿不起自己的强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晋军潮水般地突入牙城。安重荣被晋军俘获,送至石敬瑭处。
石敬瑭看着昔日的悍将,不觉百感交集,却又无话可说,只得敕令将安重荣斩首,并将他的首领快递给小爸爸耶律德光报功。
在中原王朝与契丹异族攻守之势逐渐转移的五代中后期,在契丹强寇面前敢于发出豪言奋起抗争的安重荣就这样悲壮地去世去了,只留下他的忠魂毅魄仍旧卫护着贰心中神圣的中国。那个出卖灵魂给异族的石敬瑭在不久后也去世了,他那肮脏的魂魄必将无所归依,后世的人们只会对他千夫所指。这便是中国历史,她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她的煌煌史册中,哪怕是像铁胡这样难酬壮志的蹈海英雄,依然千古留喷鼻香,大概这便是中国历劫五千年不朽的精魂所在。
END
图片来源于网络
喜好本文/作者,文末讴歌一下表达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