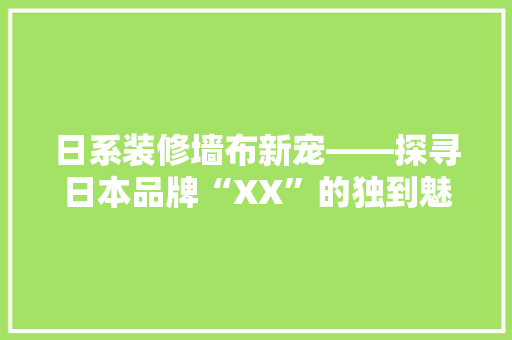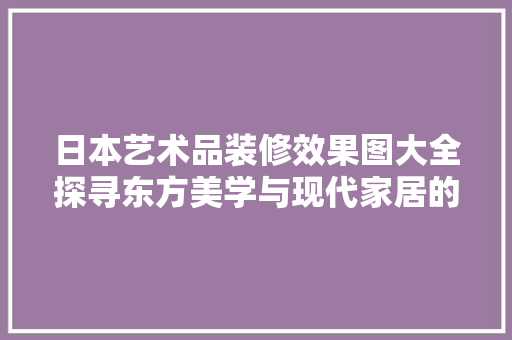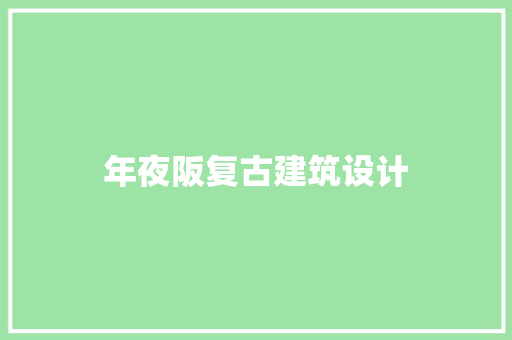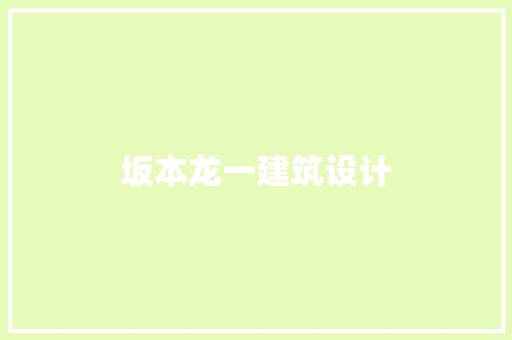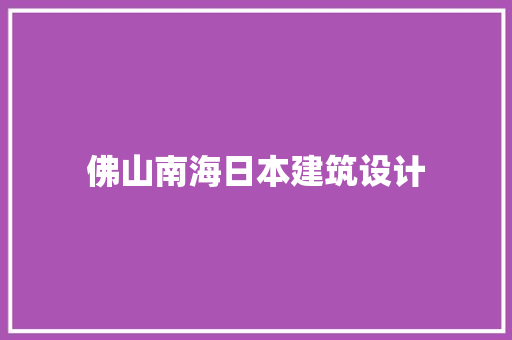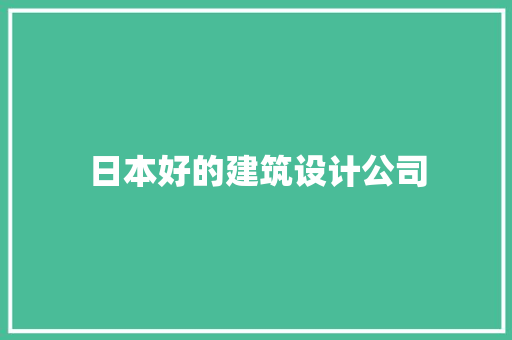花开时节
独特的平民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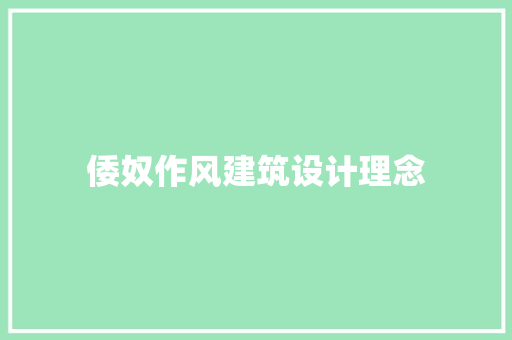
13世纪之前的日本美术基本上以佛教美术为主,从安然时期开始向世俗美术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题材上由人对神的更换,而且从不雅观念上开启了从冀望“来世”到着眼“现世”的先声。浮世绘将视线投向下层社会的平民百姓并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从神佛的庄严到贵族的闲适,再到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意味着日本美术审美取向的根本性变革。经济主导权的转变从客不雅观上匆匆使日益富余的平民阶层成为新兴社会力量,为浮世绘的发展供应了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
江户时期的平民阶层虽然在经济上有足够的能力,但武士阶层为了掩护其统治,采纳高压政策,导致市民文化在表现办法上具有某种弯曲性,即以对“生”的表述蕴藉地传达真实的生理意蕴。江户美术也由此呈现出与以往传统美术不同的样式与性情。“这种民间性情表示出对生命希望的需求,对实现平等、和谐社会的心愿两方面的内容,以各种生活办法和文化样式形成了日本民族生活史的特点。”
浮世绘也由此形成隐喻性这一大特点,类似本日所说的“脑筋急转弯”,借用“猜谜画”的手腕,以特定图像或笔墨的谐音表示另一种意思,表示辨识的意见意义性和诙谐感。画面包含比喻、遐想等元素,令不雅观者在费心揣摩之后恍然大悟。这些隐蔽着的元素和日本民俗、文化包括措辞都有密切联系,这也是江户人对浮世绘津津乐道的主要缘故原由。预测这种联系是江户民众的一大乐趣,但对当代人来说则富有寻衅。因此,浮世绘并非只是纯挚画面靓丽,也是充满意见意义性的民间聪慧。
浮世绘画师紧张来自民间,他们面对的受众大多是没有多高文化教化的普通市民和劳动者,其间虽不乏有学养的贩子,但从总体上看,依然是一个低文化层次的群体,从实质上不同于过去以宫廷贵族为主的文化受众。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从题材选择到形式表现上关注点的不同。
浮世绘作为面向市场的商品艺术,其先天的“非纯艺术性”注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从形式和内容迎合大众需求。由此,浮世绘在审美意见意义上明显有别于传统的大和绘,从铃木春信笔下永恒的青春少女到东洲斋写乐真切的演员肖像,从喜多川歌麿文雅的美人画到歌川广重的抒怀风景,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大众情怀,这也这天本美术从宫廷走向民间的一个光鲜特色。
强烈的生命意识
浮世绘并非纯挚的世俗风情画。以风景画为例,不仅表现了各地名胜,也表现出旅人的心情。浮世绘对民间生活办法的表现,其所蕴含的丰沛文化质素以及日本文化中的生命成分,表示了浮世绘的核心意义。
总起来说,浮世绘的实质精神在于表示了一个“粹”字,它是一个富有深刻精神内涵的观点。日文假名“いき”,日语汉字“粋”,还可阐明为“意气”,因日语“粹”的发音和“意气”相同。既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又有华美、诙谐的含义,具有内涵深刻且宽泛的市民文化观点。日本人文学者九鬼周造在《“生”的布局》一书中指出,“粹”有三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媚态”,这里特指与女性交往时所表现出的品位,是“粹”的根本布局;其二是“意气”,是江户仔的基本精神面貌;其三是“超脱”,日语称为“谛”,基于对命运的认知而生发出的洒脱。因此,“粹”与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空想主义道德不雅观互为因果,忽略威信,成为影响深远的精神存在,从整体上支配着江户市民个人品质的形成。
对镜
对付江户平民来说,吉原美人与歌舞伎明星所构成的风骚天下无异于“粹”之美的详细形态,由此也成为浮世绘不竭的题材之源,是平民阶层在得到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能力之后表现出来的审美办法和文化不雅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浮世绘创造了平民社会的历史。历经长年战乱之后的太平盛世,平民百姓在尽情享受“粹”的愉悦之时所引发出的无限能量推进了社会创造,也是基于对“粹”的感性体验的代价创造。
日本人在接管了外来儒教与佛教文明之后,也未洗手不干,远古文化的痕迹依然存在,固有的道德不雅观念并没有改变。禁欲主义的佛教在日本也被大加“还俗”,将对“来世”的愿景变为“现代”的及时行乐。日本的原生文化更虔诚于内心的自然情绪,这这天本文化中“情的与共感的”性情。“浮世”一词反响了享乐人生的社会现实,浮世绘美人画和歌舞伎画所描述的便是江户地区紧张游乐场所的人物,表情与气氛都流露出日本人开放的性意识。
“浮世绘的这个天地是有限的,却有着令人瞩目的完全性。在一个半世纪里,成为这个民族生活的一壁镜子;确切地说,它以无穷无尽的变革性反响出该民族的这一分外阶段,进而又描述出那种生活的背景,乃至描述出它所根植的过去的渊源。初看上去,这个画派彷佛是自我封闭的。那种下层社会的创造物,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意见意义和快乐而存在着,彷佛它与使古老艺术受到熏陶的哲学、学术、宗教诸领域均毫无关系。但是当我们仔细一看,便创造它与全部的民族精神遗产多么轻松而又自然地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借助浮世绘这把钥匙来开启日本文化的心灵之窗。
东京拾二题 龟户神社
崇尚自然的文化生理
“日本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的美学支撑的。”由于地理与景象的缘故原由,日本人自古就形成了崇尚自然的天下不雅观,并由此孕育了崇尚自然的造型与色彩的美术样式,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理性精神。由自然蜕变而来的造型不雅观具有流动的、模拟植物曲线的有机形态。
有学者将日本文化表述为“稻作文化”或“象征文化”,比较准确隧道出了日本文化的特色。日本画家东山魁夷指出:“特殊是对身处丰富的自然环境之中、常常满怀深情地不雅观察四季变革状况的人们来说,对自然产生亲切感是天经地义的。”东山魁夷回答了日本民族对大自然的亲近感的社会历史缘由,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则从人文生理的角度做了详细表述:“广袤的大自然是神圣的灵域⋯⋯高山、瀑布、泉水、岩石,连老树都是神灵的化身。”日本人以“自然感悟”或“自然思维”在大自然中孕育了自己的精神和艺术。日本神玄门的基本理念是“泛灵论”,即在与大自然长期亲和相处的过程中,将每一自然物都视为“有灵之物”。感悟自然不仅成为日本人精神自察的主要办法,而且也是审美活动的主要内容。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通过剖析研究人类史前艺术征象,提出了著名的“原始思维”理论。他创造人类在幼年阶段不具有抽象概括的思维能力,而是通过对形象的“直不雅观把握”或“整体直觉把握”的办法来认识天下。根据这一理论,原始初民具有一种与当代人类完备不同的“原始思维”办法。因此,在他们对各种事物相互之间关系的理解中,表现出一种“互渗”的特色,也便是将所有事物都视为同一性子且都同样富有灵性和生命。在他们看来,人类与自然万物是平等并融为一体的,因此人类能接管来自树木山川等自然界的信息,树木山川也同样会对人类的意念有所感应。
日本美学家户井田道三把日本民气中的原始残余称为“原始心性”,并指出在日本人的思想不雅观念里,还残留着浓厚的未开化人的意识。正如绳纹文化在当代日本人的潜意识深处的残余那样,日本民族的“自然感悟”从实质上来说实在便是“原始思维”的残留。
由自然蜕变而来的日本造型不雅观也就具有了流动的、模拟植物曲线的有机形态,包括斜线的构成、抽象的装饰性、平面性和夸年夜的色彩等诸多观点,并由此孕育了崇尚线条造型的设计样式。
黑船屋
日本传统的和歌、俳句等,便是通过对自然的吟颂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绪。浮世绘风景画与花鸟画最直接地表达了江户平民亲近自然的心态,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独特自然不雅观的鲜活载体。葛饰北斋激情写实的山水和歌川广重温存达意的风土,无不呈现出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情怀。歌川广重之以是被称为“乡愁广重”,正是由于他的风景画表达了日本人的心性与大自然的应答关系,由此也成为“物哀”的最好注脚。
浮世绘的样式契合江户平民喜好小艺术品的审美意见意义,日本民族历来偏爱小型化的物品,从《源氏物语绘卷》到浮世绘都不过盈尺之间,因此“浮世绘画师的构图能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和绘这天本文化迁移转变期间涌现的民族绘画样式,往后被用来总称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绘画。风尚画实际上只是题材的观点,可以说浮世绘在绘画样式和审美情趣上继续了大和绘的风格,而在题材上则表示了风尚画的内容,表示了从公卿贵族到平民百姓的审美意见意义的演化。
非对称性构图
非对称性构图是给西方带来震荡的日本美术魅力之所在,富有跳跃感的旁边不屈衡的构图,是与日本人的自然不雅观和生命意识息息相关的审美意识。浮世绘通过构图的变革、人物的动态设计和相互间的对应、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手腕,建立了完全的程式化手腕,与俳谐、文学、戏曲等平民文艺形式有共通的审美意境。浮世绘还以“三联画”“五联画”等办法扩展画面,以人物为中央的构图灵巧多样。
在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非对称、不规则、不匀整的背后,实际上潜隐着的是更对称、更规则、更匀整的东西,这会产生一种独特的空间之美。由于在人的视觉影象中,不连续的形状具有增长的潜质,能够依据不同的生理履历形身分歧的完全形态,从而扩展和丰富可见形的表现力。完全的形状却是固定和静止的,无法为不同的、变革着的视觉影象供应想象与增长的空间。
日本桥( 夜明)
佛教文化在公元6世纪往后传至日本,日今年夜多数寺院从l3世纪开始以非对称性手腕一改中国建筑构造的对称模式。从日本神社建筑中也可看到其古代建筑所具有的简素、谐调以及非对称的基本性情。推而广之,日本的皇家及庭院建筑、茶肆等在空间布局上并非直接诉诸感不雅观,而基于禅宗的精神性,更多地以冥想式的美作为最高造型原则,具有简素、孤高、自然、静寂和不对称性等特色。
在日本,不完备的东西被奉为崇拜的工具,由于它具有变革的可能性。为了让想象力能自由地去完成它,人们故意让其保持不完备的状态。浮世绘的另一个紧张特色“局部放大”手腕也由此而来,即将画面主体极度推近,导致主体部分被画面割断,随着主体完全性的生理暗示,使表现空间延伸到了画面之外。在日本人看来,不完全的形式和有缺陷的事实都更有助于传达精神意念,人们通过在生理上和精神上对不完全景物的完全化这样一个过程,更能靠近于创造工具的实质精神。
从葛饰北斋与歌川广重的浮世绘风景画中可以看到许多旁边不对称、留有大面积空缺、画面主体倾向一边乃至被割断的构图。浮世绘从安然期间的绘卷物、织物等借鉴了这种技法:从画面中心到主体富有动感的构成,紧张表现在构图年夜将工具以看不见的潜在斜线相连接,这是从日本古代就开始形成的独特表现技法。日本的屏风画与色纸、短册、挂轴等,以及日本装饰画中的空间构成都得到多样化的处理,在和服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灵巧多变的倾斜构图设计。
抽象的装饰性
日本美术长于将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抽象化,在不雅观察、表现工具时充分夸年夜其造型特色使之进一步纯挚化,作为“形”加以整理并抽象化。常见的装饰性图案中,起初是菱纹、角纹、鳞纹等几何造型,然后纹样更加大略化、更富有装饰性,被作为底纹利用。“抽象性”“精神性”这天本工艺美术表现中的主要成分,如《源氏物语绘卷》便是安然时期贵族文化的代表,华美的贵族服装也从一个方面反响出当时装饰艺术的最高水平。
12世纪初北宋末年出版的《宣和画谱》中写道:“日本国,古倭奴国也,自以近日所出,故改之。有画不知姓名,传写其国景致山水小景,设色甚重,多用金碧。考其真未必有此,第欲彩绘璨烂,以取不雅观美也。”这是对当时日本屏风和绘物卷的直不雅观评价。
《宣和画谱》所记述的“景致、山水、小景”即指大和绘,“金碧多用而不真”的批评,明确指出了日本美术的特色,即从追求纯粹的视觉美感出发,表现绘画性、装饰性和设计性。大和绘在将唐绘日本化的过程中,不仅是绘画主题的变革,更主要的是强化了装饰性、设计性的成分。中国绘画以北宋水墨为代表,山水画以可游可居为最高境界。青绿山水中对金泥的利用被移植到日本后,发展为直接将金箔植入画面,从日本安然、镰仓时期的佛教绘画中,就可以看到许多平面化、工艺性的装饰手腕。
五位裸女
浮世绘的装饰意见意义很大程度上通过衣饰纹样的图案来表现。江户时期可谓日本衣饰设计的高峰期,“大胆的色彩组合与丰富的花卉植物险些包罗万象,并精彩地将其图案化。可以说在每一套和服中都凝聚着一个美的天下”。17世纪后半叶,盛行色彩多以中间色为主,细腻而丰富;18世纪初,色彩开始趋于通亮,图案纹样纤细而华美,反响出新兴市民阶层的活力。江户中期因受到幕府禁奢令的影响,色彩与纹样都倾向素雅,和服开始盛行红黑间色的套装。浮世绘的色彩意识也在连续华美装饰性的同时逐渐趋于沉稳,这是江户风格的成熟期。18世纪中期随着浮世绘技能的高度成熟,也呼应了服装设计界的发展,周详的雕版手腕使日益繁芜的纹样表现成为可能,延续中期的素雅色调,以淡蓝、浅绿、绀茶、紫色等为主。浮世绘不仅记录了当时服装格局的演化,还细致、全面地反响了时尚色彩与纹样的面貌。
通亮的色彩
日语的“色”字基本包括五方面内容:一、色彩,即色相、彩度、亮度的成分;二、音色,声音的调子;三、乐色,日本民族音乐中的装饰性曲调等;四、姿色,边幅的觉得;五、情爱的觉得,日语将情人称为色男、色女。就色彩而言,日本学者佐竹昭广在《古代日语的色名性情》中指出,日本的色名起源于白、青、赤、黑四种颜色,也这天本人原始色彩觉得的基本色。从日本《古诗集》中记载的神话故事可见,古代日本人最初因此白与黑、青与赤的对称来表现色彩体系的。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收录了公元6世纪至8世纪间的大约4500首和歌,个中包含对颜色描写的和歌共有562首,而对赤色系与白色系描写的就分别占202首和204首,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日本先人的文化态度、代价不雅观念和审美情趣。
关于日本古代的色彩崇尚,日本学者前田雨城在《颜色:染与色彩》一书中指出:“赤”来自“通亮”的“明”字,是暖色系的色彩,“红、绯、赤、朱、赤橙、粉红”等在古代日语里都用“赤”来表达。“黑”来自“暗”字,与“赤”相反,是冷色系的颜色。“白”则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既具有某种神秘意味,表达神灵崇奉工具如白鹿、白狐、白雀等,也用来表示色彩觉得,但又不具有表征某种详细颜色的功能。“青”包含了不属于以上所述的“赤”“黑”“白”的所有颜色,包括“绿色、蓝绿色、蓝色、蓝紫色、紫色以及这些颜色的中间色”。因此,在日本人的视野中,青是一种内涵宽泛的色彩,可以看到在后来的浮世绘中青色就被大量利用。
自古以来,白色在日本的色彩体系中霸占主要地位。在日语中,“白”也可用“素”字来表示,即“天然本色”的“白”,象征清洁、通亮,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古代神话中就有“清亮心”(清洁通亮的心)的用词。因此白色不仅是色彩用语,同时还寄托了日本民族的道德神往。日本自安然时期从大陆输入白粉之后,白粉在女性扮装品中霸占了紧张地位。对白色的崇尚深刻影响了近当代日本的审美意识,并广泛渗透到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日本传统的神玄门崇尚白色,并以白色作为人与神联系的颜色。日本神社有别于中国寺庙的浓墨重彩,基本保留建筑材料的本来颜色,周边环境和关联举动步伐也都只管即便淡化人工痕迹,处处表示清纯的自然风貌。日本文化对白色的崇尚还表示在对白纸的关注上,日语中“纸”和“神”的发音相同,均为“kami(かみ)”,日本和纸具有独特的肌理和韧性,且洁白无瑕,被视为“凝聚了神灵的力量”。
浮世绘长于在黑白墨色中营造多彩的画面效果,用植物性颜料精心拓染,在和纸上渗透领悟并显现肌理,表示出透明、纯粹和滋润津润的性情,也由此被凡·高惊叹为“通亮的国度”。“日本美术虽有许多特色,但如果将其放置于天下美术中来看,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由通亮日照而产生的多彩,日本美术对天下的影响也紧张是从这个方向出发的。”浮世绘表示了日本美术对形与色的创造性追求。
【摘自:《浮世绘》 潘力/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浦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