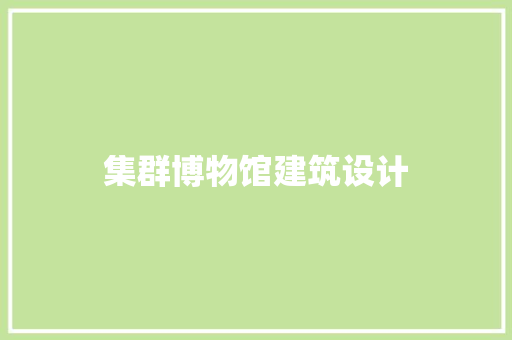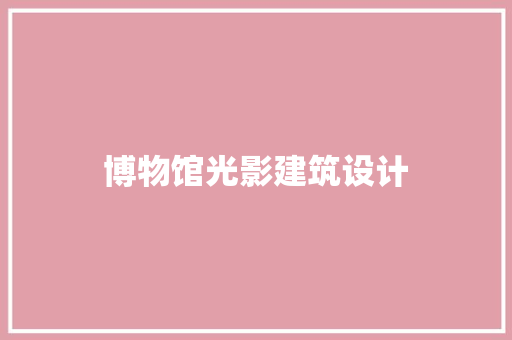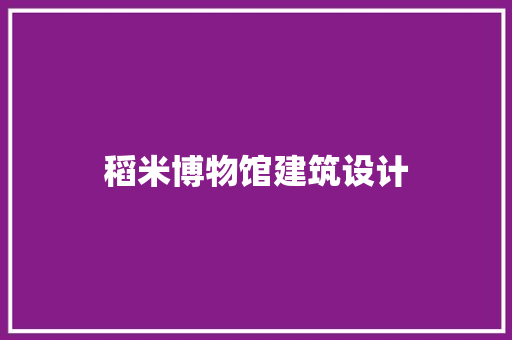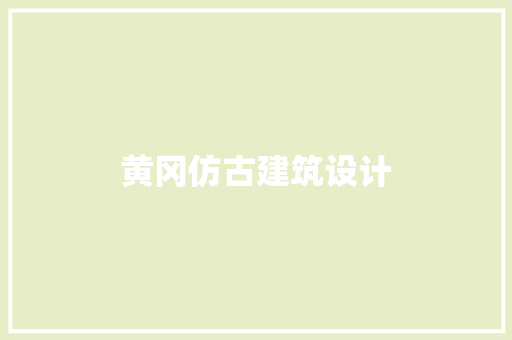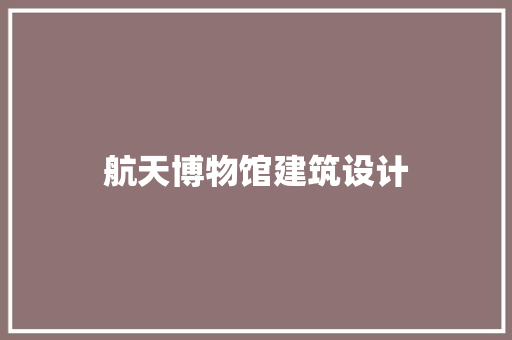转自:回响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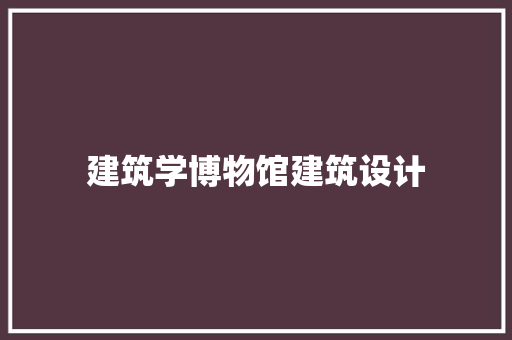
©
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博物馆正在成为越来越主要的公共空间。人们从博物馆里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空间体验。博物馆与参不雅观者之间的关系,从以往的“贯注灌注式”转变为“平等互换”。美国博物馆学家妮娜·西蒙说,博物馆最新发展趋势之一是“参与”,成为“一个不雅观众能够环绕其内容进行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互换的场所”。
建筑本就负有引发人的活力与创造力的职责,博物馆作为“文明的容器”,其建筑设计如何与参不雅观者的身心互动,便十分磨练建筑师的功力。为了增强参不雅观者对博物馆设计的感知和沉浸式体验,当代博物馆设计须要知足征象学理论的两大要素——场所感和感官体验。
左:马丁·海德格尔;右:莫里斯·梅洛-庞蒂
征象学是由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于1910年开展的一场哲学运动,他将征象学理解为“回归事物实质”。胡塞尔认为,意识既要关注纯粹的征象,也要关注人们在生活中的直接感想熏染和体验,从而把握事物的实质。二战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启示了越来越多的建筑思想家将其运用到建筑学科中。与当代建筑的呆板统一的设计有所不同,征象学强调感官体验和场所感。
本文将环绕两位当代精彩的征象学建筑师——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和史蒂文·霍尔(Steven Holl)所分别设计的科伦巴博物馆和布洛赫大楼(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新馆)作为案例。从场所的氛围营造、空间体验、细节感知体验和光影体验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建筑征象学理论是如何表示在当代博物馆设计中的。
德国科伦巴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座在第二次天下大战期间毁坏的哥特式教堂废墟上建造的博物馆,卒姆托将原有的废墟与当代建筑完美的领悟在了一起,将宗教与艺术以优雅简约的办法领悟在了一起。©RasmusHjortshøj
卒姆托和霍尔均看重“多感官”设计。他们认为要真正感想熏染建筑,参不雅观者的体验尤为主要。当人徜徉在建筑中,利用所有感官去感知建筑中的光与声、重叠的视角与细节,才能实现建筑征象学的真实体验。卒姆托以更加“感性”的办法阐明海德格尔的征象学。换言之,卒姆托通过建筑空间设计和形式来转变个人体验,传达出最纯粹的“氛围”观点。
霍尔总体上认同梅洛-庞蒂的征象学,霍尔认为建筑因此故意识的办法并通过不雅观念或观点构建的。因此,霍尔常日在他的项目中采取“交织”和“视差”观点来探索这一想法的征象学潜力。与卒姆托分开逻辑过程的设计方法比较,霍尔非常强调项目的观点逻辑与用户感知之间的主不雅观联系。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扩建领悟了建筑与景不雅观,史蒂文·霍尔以此打造一个体验性的建筑,当参不雅观者经由扩建部分时,他们将体验光、艺术、建筑与景不雅观的流动,从一层到另一层,从内到外。©Andy Ryan
场所是指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的结合。它是特定场所独特历史文化和环境特色的反响。卒姆托主见将建筑融入园地环境中。他的氛围观点是关于建筑如何与其环境融为一体。
科隆巴博物馆位于科隆市中央,间隔科隆大教堂约两个街区,间隔市中央的购物街仅几步之遥。博物馆遗址位于城市两条街道的交叉口。建于科隆当地一座名为“圣母教堂”的教堂遗址上。科伦巴博物馆紧张由西侧的圣母教堂、中部的教堂文物展厅、东侧的艺术展厅三个功能区块组成。科伦巴博物馆南立面历史墙的内部是考古发掘区,容纳了教堂的入口,毗邻Brooken街。新博物馆的入口位于建筑西侧,紧邻Kolumba 街。
卒姆托从两个方面处理了科伦巴博物馆与园地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他将新建筑立面与环境融为一体。博物馆南立面保留了科伦巴教堂哥特式窗格,新定制的瓷砖直接与断壁相连,构成了新建筑的立面。另一方面,卒姆托将新空间与原有园地空间进行了整合。
卒姆托 科伦巴博物馆内部
和卒姆托一样,霍尔也认为“场所”在建筑设计中起着决定性的浸染。他的锚定观点从征象学的角度磋商了建筑与场所之间的关系。
为了让建筑与园地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霍尔认为建筑不仅要与园地的独特体验融为一体,还要融入全体园地的文脉。在详细处理园地和建筑功能方面,霍尔认为设计时须要考虑景不雅观、日照角度、通道和流线这四个成分。同时,结合建筑空间的延伸,达到连接建筑与园地的目的。
布洛赫大厦采取了霍尔创造的“石头和羽毛”的观点——“石头”代表了厚重、封闭的旧馆,而“羽毛”则象征着轻盈、开放的新建筑。新的扩建像羽毛一样散落在园地的景不雅观中,沿着园地原有的南北轴线谦善地延续,表现出对园地历史和文化的尊重。
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老馆)封闭的静态和理性比较,布洛赫大厦(新馆)是开放的、动态的和自由的。布洛赫大厦的多个入口的设计增强了游客的可达性和连通性。
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新馆内部©Andy Ryan
两位建筑师的在设计场所有着不同的理念:卒姆托在科伦巴博物馆设计时采取“融入”原园地的办法;霍尔在布洛赫大楼园地设计中则将新馆建筑“锚定”在场所中,将建筑与场所的体验交织在一起。霍尔创造了良好的建筑可达性和户外开放流线,鼓励游客参不雅观,授予人们自由行走和近间隔参不雅观的权利。可以看出,以上两种办法对付建筑师创造“场所精神”都非常有用。
彼得·卒姆托设计的新建筑将现有碎片的总和转变为一座完全的建筑。通过采取原来的操持并在废墟上建造,新建筑成为建筑连续体的一部分。
建筑空间为每个参不雅观者创造了独特的感知印象,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思维。当体验到空间所呈现的独特氛围时,参不雅观者们自然会被吸引。
在科伦巴博物馆设计中,卒姆托没有为游客参不雅观设立指定路径,他利用光“勾引”人们以轻松的办法溜达在不同的空间,从而唤起人们能够自由不雅观光的愉悦感。
并且,卒姆托利用多感官设计为游客打造了一个勾留和冥想的体验空间。考古发掘区中,遗址通道上有一座弯曲桥,供游人自由行走,并设有安全扶手,供触摸和倚靠。除了知足视觉、触觉、听觉之外,还包括嗅觉。当烛炬燃烧时,气味会在遗迹展览区的大空间中扩散。科伦巴博物馆多感官、动感和连续空间的支配相结合,让参不雅观者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世纪前的古老教堂中。
科伦巴博物馆从场内哥特晚期教堂的废墟中升起,卒姆托很喜好这种“融入”原园地的办法。
在空间设计方面,霍尔先容了他的视差理论——身体运动及其在项目实践中带来的感知体验。他在视差理论中利用了“感知”一词,指的是人身体运动的变革产生对天下和自我的整体认识,这也是梅洛-庞蒂对身体作为通向天下的门户的独特见地。他认为,身体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空间尺度,其对空间的感知取决于其自身在空间中的运动,从而产生视差。
霍尔在他的设计中看重人们的感知,将人类对建筑的感知与详细的建筑元素结合起来,帮助他设计空间。霍尔认为,人类的感知不仅涉及视觉体验,还涉及触觉、听觉和嗅觉。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当代艺术研究中央
霍尔认为最主要的建筑材料,不是混凝土,不是木材、钢材,而是没有形状的——光,他致力于捕捉光芒一直变换的特质。
霍尔解构了传统博物馆规定、单向的参不雅观流线形式。相反,霍尔采取了清晰灵巧的流线为参不雅观者在空间中自由行走创造了新机会。每个展厅之间也有一定的水平间隔,当参不雅观者到达一个展厅的边缘时,一眼就能看到下一个展厅的空间效果和陈设,吸引人们连续前行。
我们不难创造,这两位建筑师通过不同的设计手腕来达到让参不雅观者在空间中自由行走的目标。卒姆托利用光来勾引游客自由活动,而霍尔则采取开放式流线勾引游客参不雅观博物馆。
布雷根茨美术馆
卒姆托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在一个雨天首次拜访了康斯坦茨湖畔,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这个小镇本身,而是沿山路而下时,光所产生的奇妙变革,这便让我有了想要创造一个能够将笼罩在湖面上,可清晰透射光芒的薄雾吸纳进建筑的想法。”
作为塑造空间氛围的手段,材料的重量、温度、光泽、气味等能够调动人们的感官知觉感想熏染。
卒姆托的设计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重视材料本身,二是重视建筑的直接感官体验。他善于采取得当的材料及其性能并结合美学来设计建筑物。其次,卒姆托颠覆了建筑作为紧张视觉媒介的观点,更方向于多感官的表达办法。卒姆托利用材料的图案、纹理和自然气味来刺激人们的视觉、触觉和嗅觉,唤醒人们的空间体验。
霍尔常日根据反光特性和触觉来选择建筑内外部材料。布洛赫大厦的钢和玻璃构造与附近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石灰岩外墙形成光鲜比拟。该项目利用了LINIT U(一种具有缎面光泽的半透明玻璃材料),与平板玻璃的镜面反射特性不同,这种材料的特点是将周围天空或风景的颜色渲染至室内纯色墙面。
在材料的利用上,科伦巴博物馆底层立面采取了致密的长砖和附近色接缝,有助于衬托断墙的纹理和形状。遗址教堂保留了原有的墙体,融入灰白色的外壳中,通过立面与临近的建筑呼应,从而使新建筑与街道折衷同等。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透镜的双玻璃腔在冬季网络阳光加热空气,夏季则相反。通过电脑掌握屏幕和嵌入在玻璃腔体的分外半透明绝热材料,为所有类型的艺术作品或者媒体装置供应的最佳光照以及时令灵巧性得以实现。
建筑材料有助于强化与园地建立联系的目的。在科伦巴博物馆的设计中,卒姆托利用了砖、石、木等天然材料。这些材料向参不雅观者传达了它们的性情和年事,同时材料本身的质感也给参不雅观者带来了视觉和触觉的知足。在布洛赫大厦立面设计中,霍尔紧张利用玻璃和钢材。室内设计方面,霍尔采取有着凹凸纹理的石膏墙,其丰富的触感可以帮助参不雅观者与建筑建立情绪联系。
霍尔设计的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该项目由平行透视空间和一个用竹子制成的玄色夯土院墙构成的。地面一层笔直的通道逐渐变革成上方轻质构造体中蜿蜒的通道。© Sifang Art Museum
在建筑中,光因其最常见和韶光性的特色,对付营造氛围是不可或缺的。光影具有空间塑造的力量,给建筑和身处个中的人带来多种精神感想熏染。
卒姆托偏爱将自然光作为设计的一部分。他认为自然光具有精神品质,尤其是当看到光照射在物体上时,那种景象更让民气生冲动。在科伦巴博物馆的照明设计上,卒姆托紧张通过天窗和材料的缝隙将自然光引入阴郁的室内空间,从而将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结合起来。在展览空间中,中空的双层墙将自然光散射到内部。通过立面的漫反射,光芒充满了建筑物的屋顶、地板和墙壁。随着时令和韶光的不断变革,这些斑驳的光影仿佛在废墟中移动,不仅给展览空间带来了丰富的活力,也为参不雅观者营造了一种宁静的氛围。
科伦巴博物馆,卒姆托通过天窗和材料的缝隙将自然光引入阴郁的室内空间,在参不雅观过程中,随着韶光的变革,斑驳的光影仿佛在废墟中移动,营造了一种有活力又宁静的氛围。
科伦巴博物馆的二楼展厅采取局部照明,结合朝向科隆大教堂及其周围环境的落地窗,窗外的景致和自然光与室内建立联系,帮助缓解游客参不雅观博物馆的疲倦视觉。同时,这些窗户还可以让游客通过看到表面的地标来帮助理解他们在博物馆空间里所处的位置。
霍尔为了达到空间与光芒的交织的目的,让建筑得到不同角度的自然采光,并与不规则的空间形态融为一体,给参不雅观者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霍尔同样看重夜间灯光的表现。在他看来,夜光和日光能给人带来完备不同的感想熏染。白天,霍尔采取自然光源和人造光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不同品质的光芒带入布洛赫大楼的画廊(如自然光、艺术照明、漫射和折射光)。到了晚上,建筑物外部被荧光灯管照亮,俨然成为了一个发光的“大型雕塑”。
霍尔设计的休斯顿当代艺术博物馆,白天与夜晚的光影变革。©Peter Molick ©Richard Barnes
与一些当代艺术博物馆采取单调均匀的灯光不同,霍尔利用柔和、漫射的自然光来营造建筑的空间感。霍尔采取一种名为“呼吸T”的巨大构造,当光芒通过波折的墙壁反射到画廊内部,形成光影渐变。光影随着韶光和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变革,给参不雅观者带来不同的艺术感知和蔼象。并且,T形墙构造许可南北光芒稠浊流入画廊,加上精心放置的聚光灯,将人们的把稳力引向画作。
霍尔设计的格拉斯哥艺术学院扩建项目,大楼内部的空间同样遵照了光影流利的方向进行布局,霍尔通过创造3个圆柱形轴光芒运动方向,被其称为“被使令的空间(Driven Voids)”,使建筑、空间和光之间领悟成一体,同时也将屋顶上的光芒更好地引入到室内及地下区域。
卒姆托和霍尔的征象学思想,直接表示在他们的博物馆项目中:
卒姆托强调对场所的尊重,并与多感官空间设计相结合。在设计过程中,为了实现人们对园地的认同,他致力于从园地废墟中提取精华,从而营造出基于特定历史文脉和人类感知的空间氛围和园地环境。
霍尔的实践紧张表现出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在他自己的征象学不雅观念中,他将建筑与征象学履历结合起来。其次,他通过设计将其建筑融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中。霍尔探索各种感知对建筑体验和感知的影响,将人的运动、光影变革和材料细节的感知变革融入到博物馆空间的设计中。
征象学提出的“事物本身的回归”,也可以成为建筑设计时的主要出发点。为了丰富利用者的多感官体验,建筑师须要从人的履历出发,而不是从自上而下的形式出发。在未来,建筑征象学“多感官”设计有着非凡的潜力,可以帮助建筑师利用到不同类型的建筑设计实践中。
上:卒姆托的布雷根茨美术馆夜景
下:霍尔的格拉塞尔艺术学校夜景
©
撰文
田欣悦
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硕士
平面设计 / 排版
俊俊&申强
内容监制
子溪
新媒体运营
Jean